世界候鸟日:邀4位一线工作者,分享候鸟保护实践与思考
随风起舞,振翅翱翔。候鸟,被誉为“天空旅者”,它们穿越崇山峻岭,历经季节变换,描绘出生命的灵动轨迹,在自然的宏伟篇章中谱写出生机勃勃的篇章。为了守护这份生机与活力,众多研究者与保护者潜心耕耘于候鸟保护与研究的领域,用无尽的热情与执着,照亮了这些“天空使者”的迁徙之路。
5月10日是每年的世界候鸟日。当天,我们荣幸地邀请了四位致力于候鸟保护工作的前线人员,他们将为众人讲述自己在保护候鸟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和深入思考。
湖是大家的,鸟也是
介绍人:来自江西余干县的康垦鄱阳湖渔鸟生态保护派出所,江西余干县公安局的民警 张世恩
站在鄱阳湖畔的草地上,目睹着成群的白鹤在天际翱翔,那些年来与“天空使者”共度的点点滴滴依然清晰如昨。今年,渔鸟派出所已步入第四个年头,而我在这片土地上工作也已四年。从起初的打击非法捕捞的“水上卫士”,到如今成为守护鱼鸟的“生态守护者”,我的身份已不再仅仅是执法者,更是“生命走廊”的建造者。
2021年2月,我国首个以“渔鸟”为名的派出所正式揭牌。长江实施“十年禁渔”政策后,鄱阳湖地区遭遇了新的考验:候鸟的栖息地与人类生活区域相互交织,生态保护工作迫切需要一支更加专业、专注的队伍。面对62公里的湖岸线和640平方公里的水域,渔鸟派出所肩负起守护人、鸟、鱼和谐共生的家园的重任。
巡湖是我们的日常工作。鉴于湖岸线漫长、水域辽阔,仅凭人力进行巡查,确实难以全面覆盖。因此,县里加大了投资力度,建成了“智慧鄱阳湖”生态监管系统。该系统配备了7架光电监测设备、4座无人机场以及463路高清监控,形成了严密的天罗地网。一旦系统发出预警,湖面出现可疑船只,公安和渔政部门将迅速联动,大约十来分钟内即可抵达现场。借助高空瞭望设备,我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15公里开外候鸟觅食的情形,宛如拥有了千里眼一般。
过去四年里,我们成功救助了22头野生动物,其中21只是候鸟,还有1只是麂。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们接到民众的举报,称有人在湖区内布设了捕鸟网。我们深入到齐膝深的泥沼中,经过超过两个小时的艰难探寻,最终发现了3张长达20余米的捕鸟网,网中悬挂着3只生命垂危的白琵鹭。我以棉质警服轻柔地包裹着小鸟,将其带至派出所的临时救助点,细心地喂食葡萄糖水,并使用吹风机缓缓吹干它们的羽毛……直至凌晨4点,随着最后一只白琵鹭缓缓抬起头,我们紧绷的心终于得以放松——这一夜的辛勤付出,实属值得!
我们曾设立了一个候鸟的“托儿所”。在去年的冬季,我们在巡查湖泊时,意外地发现了四只年幼的天鹅,它们似乎在迁徙途中与父母失散了。我立刻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并在湖边划出一片安全的水域,每日投放玉米和水草。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附近的成年天鹅群自发地担当起了“保姆”的角色,带领这些小天鹅寻找食物。经过两个月的时间,这些“幼儿园的孩子们”终于与队伍一同向北迁徙。
今年开春之际,一只受伤的东方白鹳成为了我们这里的“特殊来宾”。它在康山水域不幸被渔网紧紧缠绕,导致左翼遭受了严重伤害。我们特地邀请了省里的专家为其进行治疗,并每日细致地记录下它的康复进程。随着对环境的逐渐熟悉,这只白鹳与我们人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康复期间,它常常跟随巡湖的快艇四处游荡。当放归的那一天到来时,它在空中盘旋了三圈,仿佛在向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
鄱阳湖的生态环境近年来持续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在此栖息。余干公安部门通过在微信群里普及护鸟知识、深入学校举办“小候鸟课堂”等活动,使得保护鸟类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昔日里,部分渔民曾认为鸟类会捕食鱼儿,但时至今日,许多放弃捕鱼的渔民已转变为护鸟志愿者,曾经的捕鸟高手老周便是其中一员。他对各个候鸟栖息地的位置了如指掌,为保护工作贡献了诸多力量,去年更是协助我们成功救助了两只灰鹤。
湖水属于大家,鸟儿亦是如此。瞧,当夕阳缓缓西沉,鹤群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翩翩起舞,这画面便是我心中最为绚丽的景致。我们所守护的,不只是鸟类,更是我们鄱阳湖的精气神。
AI加持下,更多“新朋友”跨越山河
讲述人:云南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工程师 张志中
滇池位于东亚至澳大利西亚的候鸟迁徙路径上,是众多候鸟冬季栖息的关键场所或迁徙过程中的重要站点。每当初冬降临,清晨的轻雾尚未消散,滇池的湖面上便响起了红嘴鸥的鸣叫声。随着春天脚步的临近,气温逐渐回暖,红嘴鸥们便告别了昆明,踏上了北归的征程。到了五月初,在滇池的海埂东码头,我们仍能目睹一小群红嘴鸥在此逗留,它们或在湖面上尽情嬉戏,或在蔚蓝的天空中自由翱翔。
身为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的一员,我亲历了科技在候鸟监测与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滇池这片水域,正逐步演变成为东亚至澳大利亚迁徙路线上的科技护鸟示范点。
在观察鸟类时,我们应当使用何种设备?很多人可能首先会想到望远镜。过去,我们的观测活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然而,现在我们已转向更为先进的手段。请注意,在AI驱动的鸟类观察系统中,高清摄像头与麦克风正于滇池的数个示范区域实时记录着鸟类的活动情况。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我们不仅能够轻松地辨别图像中的各类鸟类,还能通过声纹图谱系统实现“听声辨鸟”的功能,甚至能够精确识别幼鸟羽毛的细微渐变纹理和色彩斑点。
值得指出的是,借助无人机进行空中巡航并采集影像,显著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这些无人机通常在距离水面约80米的空中飞行,能够在短时间内高效完成对密集鸟群的繁杂数量统计。将收集到的数据同步至观测系统后,系统会进行简单的自动分析,从而揭示出部分鸟类的活动规律。在2024年,我们借助这一系列系统的持续观察,大致了解了红嘴鸥到达和离开滇池草海南部水域的确切时间点。通过AI技术的恰当运用,我们显著提升了滇池区域鸟类多样性的监测速度,这一成果为滇池迁徙路线上的候鸟观察和研究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
利用无人机进行空中巡逻,我们有望提升劝导工作的效率,对那些不文明的观鸟行为予以制止。同时,无人机从高空捕捉到的海鸥密集群落的影像资料,有助于公众更直观地认识鸟类的集群行为,并将尊重野生动物自由活动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我们计划在滇池周边增设新的鸟类智能监测站点,并且将积极与国内其他地区的鸟类智能监测站点进行交流与学习。展望未来,我们期望借助先进的智慧监测技术,能够发现更多来自遥远山川的“新伙伴”,它们将飞跃千山万水,抵达滇池。
十年如一日守候“老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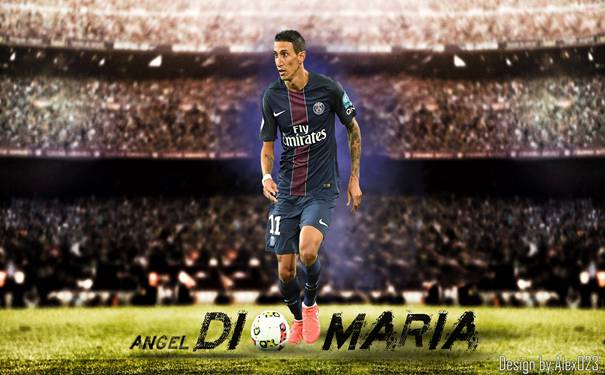
讲述人:湖南桂东县林业局南风坳候鸟保护站护鸟员 熊福良
南风坳坐落在湖南与江西的接壤地带,成为了我国内陆地区最重要的鸟类迁徙路线之一。在每年的春秋季节,数以万计的候鸟途经此地,进行南北迁徙。自2014年起,我加入了“湘赣两省千年鸟道护鸟红色联盟”,自此便始终陪伴着山林中的这些“老朋友”,未曾远离。
初涉此行那年,我和同伴们一同跋涉于山间,夜深人静时分,手持电筒,穿梭于林间小径,裤腿被露水浸得湿透。忽然,头顶响起“啾啾”的鸣叫声,我抬头仰望,在月光的映照下,一队白鹭正振翅高飞,掠过树梢。队友低声对我说:“它们历经数千公里长途跋涉,我们必须保护好这段旅程!”
自那之后,我详尽地记录下各类鸟类的鸣叫声、迁徙周期以及它们的生活环境。白鹭偏好于稻田和河岸地带,常常以散居的形式觅食,而相思鸟则更偏爱昆虫、植物的果实与种子……
2017年的寒冬,我在巡山途中抵达土地池,忽见一只白鹭,其羽毛因露水而湿润,落在我的肩头。它身体蜷缩,冰冷的露水使羽毛粘连成团,爪子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我察觉到它的疲惫,急忙从口袋里取出米粒喂食,并用干毛巾细心地擦拭它的羽毛。随着它振翅高飞,转身回望,发出清脆的鸣叫,我心中突然涌起一股与这生灵的默契之感。
2023年10月10日夜晚,护鸟站值班室外笼罩着浓重的黑暗。大约在晚上九点钟,窗玻璃上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撞击声,我们立刻走出室外,只见一只夜鸢静静地躺在地上,毫无动静。我轻手轻脚地把它抱进值班室,放在火炉旁边,给它喂了些水,并与之交谈。不久,夜鸢开始缓缓地移动,嘴里发出“啾啾”的声音,仿佛在表达感激。大约过了半小时,夜鸢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振翅高飞,消失在夜空中。
近年来,护鸟站日益成长壮大,其所在地的青竹村亦焕然一新。山林中安装了二十余台高清摄像头,设立了观鸟平台和科普馆,并为部分珍稀鸟类配备了GPS定位追踪器。每当迁徙季节来临,众多观鸟爱好者手持相机纷纷前来,成群结队的中学生到此进行研学活动,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此领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愉悦时光。来自长沙的游客经常在微信上向我咨询:“老熊,那里的鸟儿是否繁多?我打算带朋友前来观赏鸟类、入住民宿,以及品尝桂东的美食。”
一批批迁徙的候鸟在此地来来往往,离去又返回,在这片茂密的山林中,我见证了长达十年的“人与鸟共处”的时光。如今,我已步入古稀之年,每当我登上土地池,远眺连绵起伏的青山,聆听此起彼伏的鸟鸣,凝视山下排列有序的百家民宿,心中仍涌动着青春的活力。站在护鸟站前,我期待着与我的“老伙伴”们重逢……
为候鸟打造舒适“服务区”
讲述人:天津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 韩克武
天津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东亚至澳大利亚迁徙路线的关键节点,成为众多候鸟的首选栖息地,每年约有五十万只候鸟在此地停歇。然而,多年前由于水量锐减,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使得途经此地的候鸟只能带着遗憾继续前行。
2017年,得益于宁河区政府的鼎力相助,我们对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实施了全面的生态修复工程。近年来,我们进行了水坝的更新改造,并疏通了补水通道,构建了三级水体网络,能够随时向湿地内部输送水源。如今,保护区的湿地水域面积增长了50%,水质显著改善,生态功能得到了有效恢复,植被面积更是增长了三万亩。
在优化湿地整体生态环境的过程中,我们在特定的“服务区”内为迁徙的候鸟设立了温馨的歇脚点。我们精心构建了100个生态岛屿以及超过1万亩的浅水区域,为各类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觅食空间和繁殖基地。
游禽和涉禽在过境时,各自栖息的环境有着显著的差异。以天鹅为例,它们偏好生活在水位大约30厘米的环境中,而像黑尾塍鹬这样的迁徙鸟类,仅需10厘米的水深即可。自2019年起,我们每年秋季都会借助水利设施和保护区地形的高低差异,实施科学的水位管理,以构建多样化的浅滩栖息地。同时,我们也会依据迁徙季节候鸟的迁徙习性,对水位实施灵活的调整,确保这些“鸟类朋友”在七里海能够享有舒适的居住体验。
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如今景象焕然一新,鸟儿归巢,水质清澈,芦花随风飘舞。与十年前相比,鸟类种类从182种增至258种,数量也从二十万只上升至五十万只。那些曾消失十数载的震旦鸦雀、文须雀、北长尾山雀、黑天鹅、黑嘴琵鹭等鸟类,如今纷纷回归七里海。这一变化,无疑令人感到由衷的喜悦。
去年,我们成功推出了天津地区首个“天空地”综合监测体系,该体系集成了动物AI智能识别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并整合了区域内超过90套监测设备,构建了一个生物多样性监测平台。通过这一平台,我们能够全天候、全方位地对湿地核心区域内的动植物、人类活动以及生态环境等关键要素进行立体化监测。
截至今年五月初,七里海湿地已迎来25万只候鸟,这一数字远超往年同期。显而易见,越来越多的鸟类开始青睐我们这里的“栖息地”。展望未来,预计将有更多候鸟选择七里海作为它们停留的“驿站”。
记者郝泽华、周梦爽、李玉兰、王洋、胡晓军、徐鑫雨、禹爱华、龙军,以及通讯员薛静迪和郭建东联袂报道。

